冯书生:梁漱溟的道德哲学及其时代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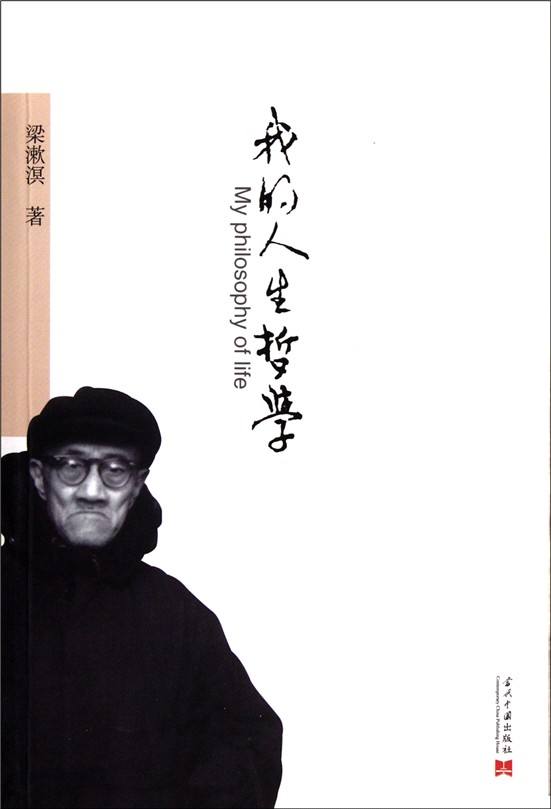
梁漱溟先生自述一生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一是中国问题。关于中国问题,梁漱溟先生的思路是认识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写有《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等著作;而关于人生问题的思考,则有《究元决疑论》(1916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人心与人生》(1975年),同时还有一本由其学生记录整理的谈话录《朝话》 (1937年)。其中,关于《人心与人生》一书的构思和撰写始于1926年,于1975年最终完成,贯穿作者一生主要时间。而之所以持续那么时间,梁漱溟先生的解释是由于中国问题的迫切性,所以不得不延迟了对人生问题的思考 。诚然,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大问题,一个需要火热的政治实践,一个需要偏身一隅的冷静思考。但是梁漱溟先生最终呈献给我们的相关研究文本却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了内在勾连,其联结点就是其道德哲学。简单来说,关于中国问题,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根本就在于“建设新的礼俗”。关于人生问题,梁漱溟先生的思考从人类心理出发,认为人心是人类生命的根本,人生要以人心为基础而展开。而关于人心,梁漱溟认为理性是其根本特征,其外在人生实践的显现就是自觉自律的“道德”。
一、梁漱溟道德哲学的佛教底色
梁漱溟先生一生发生两次哲学转向,一是由功利主义转入佛教哲学,二是由佛教哲学转入儒家哲学。整体来看,梁漱溟先生关于功利主义的抛弃是彻底的,但是从佛教哲学转入儒家哲学却不那么彻底,终其一生都带有佛教哲学的底色。梁漱溟先生关于佛教哲学的代表作为1916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的《究元决疑论》一文,也正是凭借这篇文章,获得蔡元培的赏识,而入北大教职。
“究元”即为追究世界之本源及其生成。梁漱溟认为所有东西哲学都不如释迦之教说的明白,要旨为“一切诸法唯是无性”,并以此立三种义:不可思议义、自然规则不可得义、德行规则不可得义。“不可思议义”即“不可说,不可念,非邪见之所能思量,非凡情所能计度”。既然世界在根本上不可言说、不可思虑、不可描述,那么世界规律便不可求。梁漱溟引《无性论》证曰:“言说必有所依,故若不依乱识品类名言得立无有是处”,而依他幻有,故学术不得真实;又晚近发现自然规律总是颠覆既有世界认知,前之所立,后之所破,“后之破坏益多,将成穷露”,故自然规则不可得。德行规则的根本在于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关系。“若心自由者则能拣择善恶等取舍之,以是故,德行得立。若心范围于有定者,则不能拣择取舍,以是故,德行则不得立。”自然规则既然不可得,所以决定论不成立,但并不能由此说明自由成立。(……待补充完善!“佛学方便论”相关内容)
二、道德是生命的和谐
在《朝话》中,梁漱溟先生指出,道德是生命的和谐,也就是人生的艺术。“所谓生命的和谐,即人生生理心理——知、情、意——的和谐,同时,亦是我的生命与社会其他的人的生命的和谐。所谓人生的艺术,就是会让生命和谐,会做人,做得痛快漂亮。” 梁漱溟先生认为普通人对道德有三种不同的误解,一是认为道德是拘谨的,二是认为道德是枯燥的,三是认为道德是日常生活之外的高远之事 。拘谨就是迁就外面,就是守规矩,但是没有内在生命力量。而道德是一种自然涌发的力量,是生命中最动人的地方。只知道守规矩,各方面都应付得很好的八面玲珑之人属于乡愿之徒。“乡愿,德之贼也。”看似有道德,其实没有把握道德的真精神,而是流于墨守僵化的道德之壳,也就是外化为伦理纲常的道德。把道德误认为是拘守纲常,自然是枯燥无趣的。“德者得也”,体道有得自然不枯燥,而是充满人生趣味。得道于心,外践于形,便实现了个体生命的和谐;同心同德,不相冲突,便实现了个体生命之间的和谐。道德也并不是高远之事,“只是在寻常日用中,能够使生命和谐,生命有精彩,生活充实有力而已” 。
梁漱溟先生在《朝话》中的道德阐释属于日常谈话性质,其内容更多地是直抒胸臆,劝勉为主,虽不乏理论的洞见与卓识,但是没有深入的系统论证,只是提出了观点。更进一步说,梁漱溟先生在这个时期的道德观是循于对孔孟荀等原典儒家和阳明学派的文本解读,以道德的内在性来驳斥道德的外在性。在道德与生命之间建立起了勾连,但是何为生命、道德在生命中的具体位置以及道德的内外在性存在何种关系,尚没有给予更具体的说明。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梁漱溟的道德观是描述体悟性的,在话语上借助原典儒家,以精英道德反对大众道德,以内在自由反对外在约束,以微小细腻反对高远迂阔,赋予道德以生命意义。(……待补充:混淆“道德”与“得道”)
三、道德作为人生的实践
在《人心与人生》中,梁漱溟先生对道德进行了系统化的阐释,拓展和完善了《朝话》中关于道德的论述,不再仅仅从内在性来看待道德,而是从内外在两个方面,也即个体和群体两个角度来完整表述。在个体方面,“道德者人生向上之谓也” ,在群体方面,道德在“务尽伦理情谊”,简称“尽伦” 。这一时期的道德观建立于其比较完整的生命哲学之上,不再是借儒家原典文本来释其体悟情怀。
(一)作为道德基础的人心
在梁漱溟先生看来,只有对人才可以谈论道德,动物则谈不上道德或不道德,动物依本能而生活,而人类既有本能的一面,亦有反本能的一面。从乎本能的一面为身,反乎本能的一面为心。
心非一物也;其义则主宰之义也。主谓主动,宰谓宰制。对物而言,则曰宰制;从自体言之,则曰主动;其实一义也。心之于物,其犹前之与后,上之于下,左之于右,要必相对待而有见焉。如非然也,心物其一而已矣,无可分立者。
于此可见,梁漱溟先生虽然区分了心与物(在人曰身),但又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心物二元论,将二者相隔绝,而是融心于物、融物于心,离物无心。而所谓人心,梁漱溟先生则是屡次提到,是指人类生命全部生活能力而说,心与生命同义。生命本性就是“莫知其所以然的无止境的向上奋进,不断翻新”,“贯穿着好多万万年全部生物进化史”,而“人类生命是宇宙大生命从低级生物发展出来的顶峰” 。其他生物生命都止步于循环往复的个体图存和物种繁衍,唯有人类生命在这一循环之外生发出许多意义来,不离本能而又超越本能。这一代表生命向上本性的人心总是会陷于其身的羁绊,若身主乎心,则为失德,若心主乎身,便为有德。但是代表着重复机械性的身,并非全无道德可言。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群体的稳定持续存在都离不开其特有的时代性和特殊性道德,这一时一地的道德就端赖于身的机械重复性。但在梁漱溟先生看来,这属于庸俗道德,并不是道德之真。“心为身用,自觉昏昏不明,殆为人类生活常态。此时若无违其社会礼俗,即无不道德之讥评。然而既有失其向上奋进之生命本性,那便落于失道而不德。”
(二)彼此互以对方为重
不管是将道德视为生命的和谐,还是将道德之真视为以身从心的人生向上,都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来观察道德的。然而,人类生命既有个体的一面,又有群体(社会)的一面,而且其社会生命要重于个体生命。人类生命从乎身则为相隔之个体,从乎心则为相通之群体。人类个体生命通于社会生命主要原因在于“人类由于理智发达乃特富于感情”,而“感情主要是在人对人相互感召之间” 。
伦者,伦偶;即谓在生活中彼此相关系之两方,不论其为长时相处者抑为一时相遇者。在此相关系生活中,人对人的情理是谓伦理。其理如何?即彼此互相照顾而已。更申言以明之,即理应彼此互以对方为重,莫为自己方便而忽视了对方。
这就是梁漱溟先生著名的“互以对方为重”的情理-伦理观,这一伦理观来源于其对中国传统社会性质的认识,在根本上属于对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概括和总结 。相对于近代西方社会的个人本位,梁漱溟先生认为西周以来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既不以个人为中心,也不以团体为中心,而是以伦理关系为中心。在这种社会中,“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 ,而“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人类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故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 。“伦理社会所贵者,一言以蔽之曰:尊重对方。……所谓伦理者无他义,就是要人认清楚人生想关系之理,而于彼此相关系中,互以对方为重而已。”
不过,在梁漱溟先生看来,“互以对方为重”只是一条非常笼统的道德原则,并不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具体的道德指导。具体如何以对方为重,还需要具体情境下的具体判断。
处在彼此相互关系中,其情其义既若规定了的,却又是有增有损,转变不定的。此即因彼此在生活上互相感召,有施有报,要视乎其事实情况如何,顺乎生命之自然而行。若看成死规矩,被社会礼俗所束缚,那至多有合于一时一地的社会道德,不为道德之真。
情理是随人所处地位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说话要看谁说,不能离开说话的人而有一句话;此即所谓“相对论”。彼此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思想就是一相对论,今后必将通行于大小集体与其成员之间。处在平时自能得其均衡,不偏一方;而遇有必要时,却又能随有轩轾,自动伸缩适合情况。
梁漱溟先生这一“相对论”的情理-伦理观对于一般人来说,在日常生活中是难以把握的,需要很高的人生修养和社会历练才有可能把握住每时每地的合宜性。能够在社会上所普遍通行的更多地是一时一地的庸俗道德。虽然梁漱溟先生区分了庸俗道德与真道德,并提倡真道德,但是并没有否定庸俗道德的时代价值,而是把庸俗道德作为通向真道德的阶梯和阶段,而且认为,随着人类的进步,最终要从道德之真转向宗教之真。
四、道德与宗教
在儒家那里,宗教是被悬置甚或漠视的,比如,“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梁漱溟先生的道德观虽然可以归宗儒家,但是其对宗教却持一种积极的姿态。在艾恺对梁漱溟先生的晚年访谈中,梁漱溟自谓是一个佛教徒,而且认为儒佛相通,也可以称自己为孔子之徒。
我承认我是个佛教徒,如果说我是一个儒教徒我也不否认。为什么呢?为什么也不否认呢?就是因为这个大乘菩萨,我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嘛,就“不舍众生,不住涅槃”,所以我就要到世间来。
这有点类似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走出洞穴之后再返回洞穴,以启迪他人。从梁漱溟先生对宗教的看重来看,将其道德观完全归于儒家,似乎又是不怎么准确的。在其道德观中,始终有宗教的一席之地。我们知道,在西方伦理思想谱系中,康德也为宗教留了一席之地。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通过悬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来确保德福一致的至善在现世中的实现或者说无限趋近。梁漱溟先生道德观中的宗教不同于康德,一方面固然是二者的宗教指向不同,梁漱溟以佛教来指代宗教,康德以基督教来指代宗教;另一方面则是宗教的位置和作用不同。在康德,宗教是附属于道德实现的条件悬设,在梁漱溟,道德有取代宗教维持社会生活秩序之功用;康德的道德与宗教是思想推理中的,梁漱溟的道德与宗教是实践生活中的。二者的相通性和可比性在于,道德都指向人的自觉自律,康德区分“出于义务”与“合于义务”,梁漱溟先生则坚持孟子对“行仁义”和“由仁义行”的区分 。
(一)道德与宗教相通相异
在《人心与人生》这部最为梁漱溟先生本人所看重的书中,道德与宗教都在后半部的人生篇章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且宗教要排在道德之前,道德最终还是要过渡到宗教。梁漱溟先生认为,宗教与道德虽非一事,但二者在人类生命深处存在相通之处,其根源在于“人心之深静的自觉”。
人之能自主其事,来从自觉之明,所以成其自觉自律的道德在此。非此不为真道德。宗教信仰要在必诚必敬,一分诚敬一分宗教信仰;否则,尚何宗教之可说?宗教、道德,二者在人类生命深处同其根源者谓此。
要言之,宗教与道德都出于人心之能静,能脱离本能的自觉思考。这是就真宗教与真道德而言。而对于日常通行的所谓庸俗宗教、庸俗道德,亦有其相通之处。其一,二者均属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上层建筑,会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其二,二者都对人类精神有慰藉之功能,亦有枷锁阻碍之弊端;其三,宗教有提升人之道德品质之功效,在欧洲中世纪宗教甚至被等同于道德 。不同之处在于,宗教提升品德要借假想之他力,道德则直接对人的品质提出要求;“宗教倾向出世,而道德则否”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先生则指出:“宗教道德二者,对个人,都是要人向上迁善。然而宗教之生效快,而且力大,并且不易失坠。对社会,亦是这样。”
(二)道德代宗教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先生比较分析了中西文化的异同。在西方,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重大的组织和维系作用,直至近代国家的建立,宗教的组织功能才逐步让位于世俗法律制度。在中国,自周孔教化之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不再依靠宗教来维持,而是走上了以道德代宗教的道路。
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这恰恰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他信,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
“道德为理性之事”,“宗教为信仰之事”,那么道德代宗教,也就是意味着理性代信仰。从西方精神的发展轨迹来看,宗教之后是科学,也就是说,西方近代以来走的是科学代宗教之路。科学的根本也是理性,科学代宗教也是一种理性代信仰。但是在梁漱溟先生看来,科学之理性代宗教不同于道德之理性代宗教。科学之理性向外,面向的是外在客观世界,道德之理性向内,面向的内在主观世界。但是不管是宗教、道德还是科学,其根据都在于人的心思作用,所以人类之初,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由于对宗教、道德、科学的着力方向不同,便有了超绝、向外、向内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文化路向,这便是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所立论表达的。科学之理性与道德之理性同为理性,而又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我们把科学理性指称为工具理性,道德理性指称为价值理性。但是在梁漱溟先生的理论体系中则有所不同,他把科学理性归为理智,理性仅仅指向道德。
盖理智必造乎“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从这里不期而开出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本来密切相连不离。譬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
理智者人心之妙用;理性者人心之美德。……理智静以观物,其所得者可云“物理”,是夹杂一丝感情(主观好恶)不得的。理性反之,要以无私的感情为中心,即以不自欺其好恶而为判断焉;其所得者可云“情理”。
可见,在梁漱溟这里,理性即道德,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苏格拉底的美德知识论。不同的是,梁漱溟以情论德,苏格拉底以知论德,二者路向不同。道德代宗教即情理代信仰。不管是道德情理,还是宗教信仰,其根据都在于人心,而人心往往会被身之本能欲望所蒙蔽,是非常不可靠的。不论信仰,还是理性,若要稳定发挥统一人心、组织社会的作用,都离不开相应的制度约束。世界上的大宗教都有其系统严格的教会制度和组织。因此,道德代宗教,仅仅依靠理性代信仰是远远不够的。
古代宗教往往临乎政治之上,而涵容礼俗法制在内,可以说整个社会靠它而组成,整个文化靠它做中心,岂是轻轻以人们各自之道德所可替代!纵然倚重在道德,道德之养成似亦要有个依傍,这个依傍便是“礼”。事实上,宗教在中国卒被替代下来之故,大约由于二者:一、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二、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二者合起来,遂无事乎宗教。
也就是说,在中国,道德代宗教事实上是“礼”代宗教,只不过在人心根本处是道德理性代信仰。正是因为发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根基在礼俗,所以梁漱溟先生关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思路便走上了建设新礼俗的乡村建设之路,其根本处在于涵养理性,激发道德向上心。由此,看似不相关的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通过道德而连接起来。
五、伦理何以组织社会
依梁漱溟先生之见,西方中古社会依靠宗教来组织,近代社会依靠国家来组织,中国社会自西周宗法封建社会解体以来,既无庞大的宗教机构,也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得以有序运转的根据在伦理,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一方面外化为礼俗以约束行为,一方面内化为人生追求以稳定和超拔人心。在《乡村建设理论》和《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先生详细阐发了中国传统伦理名分的组织社会之用。
其一,伦理为财产分配的根据。在个人本位的社会中,财产为个人私有;在社会本位的社会,财产归社会所有。伦理社会与两者均不相同,而是有自己的特点。根据伦理关系亲疏,有共财之义、分财之义、通财之义。夫妇、父子,乃至祖孙兄弟等共享财产,为“共财之义”。兄弟之间或近支亲族间,“初次是在分居时分财,分居后富者或再度分财于贫者”,为“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邻里之间,彼此互通有无”,为“通财之义”。总之,在伦理社会中,以伦理关系的亲疏厚薄为标准,共财关系逐渐减弱;同时也看财产大小,财产越多,越要为多数人共享。
其二,伦理有政治建构之用。“旧日中国之政治构造,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如一大家庭。” 家国一体,本质上是以国为家,以处理家庭和家族关系的伦理方式来对待政治事务,把政治关系建立在伦理关系上。这一方面是把政治关系伦理化,另一方面又把伦理关系政治化,没有严格的私人领域,也没有严格的公共领域。
其三,伦理还有宗教信仰之用,解决人类生命超拔向上的精神需求。伦理有宗教信仰之用,所以才有道德代宗教的可能。梁漱溟先生认为虽然很难为宗教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一切宗教都从超绝于人类知识处立它的根据,而以人类情感之安慰意志之勖勉为事”。也就是说,宗教之用在安慰情感、勖勉意志。伦理的宗教信仰之用也正是在于此。不过与宗教不同的是,其根据不立于超绝人类知识处,而是在于伦理生活中,在于亲人之间的相互体念和心理共鸣中。
伦理有经济分配、政治建构和精神寄托之用,所以伦理能够代替宗教来组织社会。但是这都属于过去,西方自近代以来,宗教已让位于国家,而伴随传统伦理秩序崩溃而陷入混乱的中国社会却没有强有力的国家组织来出面收拾残局。在梁漱溟先生看来,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根本不可能出现西方那样有效的国家权力来治理社会,中国社会的出路在于从乡村出发培育新的社会礼俗,也就是建设新的伦理秩序。而这就是梁漱溟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初衷。
六、新礼俗构想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传统礼教社会,但同时也把中国带进了难分难统的军阀混战境地。相似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再一次陷入礼崩乐坏。梁漱溟先生依据其关于道德的双重认识及伦理社会性质的判断,认为中国传统伦理社会的崩溃不是始于辛亥,而是始于清朝。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先生曾言:“中国文化到清代的时候,表面上顶光华,顶整齐文密,而内里精神顶空虚,顶糟;外面成了一个僵壳(指礼教),里头已经腐烂。” 这个“内里精神”就是前文所讨论过的“真道德”,外面的“礼教僵壳”就是指庸俗道德。失却真道德的礼教自然是经不起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所以西洋东西进来,一下子就慌了” 。然而,人类生命是自然向上的,西洋文化虽然粗野,但却为此时的中国人带来一丝精神上的曙光,可以由此打破僵化的礼教。基于如此观察,梁漱溟先生认为,此时的中国人受西洋精神的刺激,相对于传统礼教,是积极向上的,相对于中国古人的真道德,则是向下的,西洋精神和中国传统的真道德精神之间存在内在的冲突,所以不能依靠西化来解决中国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中国传统真道德精神的传承上来,结合西洋文化的有益之处,建设新礼俗。
所谓新礼俗是什么?就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完全沟通调和成一事实,事实出现我们叫他新礼俗),不只是理论上的沟通,而要紧的是从根本上调和沟通成一事实。此沟通调和之点有了,中国问题乃可解决。
中国固有精神,在梁漱溟先生来看,就是其所念兹在兹的“相对论的伦理主义”。而西洋文化的长处,梁漱溟先生总结为四点:一是强有力的团体组织;二是团体成员对团体组织的积极参与;三是尊重个人;四是财产社会化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梁漱溟先生认为其时是中国人很苦闷的时候,一方面散漫缺乏团体组织,一方面缺乏个人的自由平等。如果着力建设团体组织,则使中国人更加散漫,如果着力建设团体组织,则自由平等难以发挥出来。这种左右为难,梁漱溟先生认为恰好可以通过中国固有的“相对论的伦理主义”来化解:“个人一定要尊重团体,尽其应尽之义;团体一定尊重个人,使得其应得之自由平等”,这相当于在传统五伦之外,“又添了团子对分子、分子对团体一伦而已” 。建设新礼俗根本上就是要建立“一个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西洋人的长处”的团体组织,这一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可名之为“情谊化的组织或教育化的组织” 。在梁漱溟先生看来,这样一个组织,是一个纯粹的理性组织,既充分发挥了人类的道德理性精神,又能够充分容纳西洋人的长处。梁漱溟先生认为,这种理性组织并非是一种不现实的空想,其原型就是中国宋朝时乡村人自己发动的“乡约”,而其所做的乡村建设就是对其进行改造,在现行政权内部逐步培养新组织,新组织长成之后,自然代替旧政权,中国问题即得解决。
结语
梁漱溟先生的道德人生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客观存在的普遍性问题,那就是个体崇高德性的普遍化困境。乡村救国运动的最后失败固然有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但在人性哲学基础上亦有其先在缺陷,即过高估计了人的道德理性。梁漱溟先生在《究元决疑论》中,曾经批评康德以德行责任反证自由存在的虚妄,以佛法说明世间并无什么道德规律,但在此文之后,却与康德分享了同一前提,即人类道德理性的无限拔高。近乎神灵的道德理性固然可以体现在某些精英人物身上,如梁漱溟先生本人,却难以普遍推广开来。也就是说,人类有理性的判断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每个人的理性能力是不同的。用梁漱溟先生的术语来说,要身随心动,而现实中更多地是心随身动。虽然社会的良序存在需要道德,但道德在实现中偏属于个体之事,群体道德更依赖身之恐惧本能。故将救国之群体政事寄托于个体理性的培养,必然虚妄。以道德立政立国固然行不通,但在政立国固的今天,着力培养推广个体道德理性于群体,则未必不是一件可行的重要之事。或许,我们可以用梁漱溟来评判中国文化早熟的口吻来评价其道德救国之理想,其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亦是一种早熟理论,而对于21世纪的中国,却具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
(冯书生: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

